发布时间:2024-01-12 16:08浏览数:5648评论数:0 收藏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数字文学(或译“电子文学”)在欧美兴起,这种新兴的文学类型不仅给读者,也给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带来了冲击。计算机媒介进入文学研究领域,在与文学的相互作用中呈现出新现象、新问题。
时至今日,学界已探索出多种数字文学审美理论,一方面从数字文学外部特征入手,坚持文学性与媒介属性,强调文学新形式、新结构,塑造新美学;另一方面从数字文学运行机制入手,强调跨学科研究,注重人机交互影响下形成的新文学风格和审美体验。
与此同时,数字虚拟时代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作为文学观念具象化物质条件和基础的书写技术和媒介自身,从书写的角度入手,也可探讨数字文学研究的新问题与新动向。数字文学研究的书写理论与跨媒介创作中的书写实践,则为未来的书写研究开启了新的进路。
王涛 专家简介
数字文学研究与跨媒介创作中的书写
作为符号的一种,从很久以前,书写与相同或不同媒介中的其他符号并不是“绝缘”的。从古代晚期到十八世纪的欧洲,相当一部分视觉艺术都再现了书面文本的主题,比如将书写文本转译为图像,或是在文本中插入体现字面义或象征义的插图,以更好地呈现书写、评注者的寓意,这在宗教经书的抄本中非常常见。反之,也有相当一部分图画当中包含文字形式的题词、题铭,有些图画则被用作书卷,作为书写符号的载体;这种形式甚至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立体派画作中的标记、印刷品(碎片)、书写片段、标签、报纸和乐谱等绘画元素中。对于这类符号学问题,除了许多神学研究有所涉及外,也有如当代艺术史学家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等人的研究可供参考。

中世纪泥金装饰手抄本圣经(插图源自网络,下同)
麦克卢汉认为,“古腾堡革命”和拼音文字的普及都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印刷文化以冷静的视觉距离,取代了手稿文化中高强度的听觉—触觉文化,将西方经验中的视觉成分推向了极端(麦克卢汉、秦格龙:186–187),但也因此在感官经验的进一步分裂中更进一步地推进了文明的革新。而如今的电力革命、媒介革命将会产生的又一次书写形式的革新,不亚于是在重返麦克卢汉所谓的“古腾堡银河系”(埃科:83)。

约翰内斯·古腾堡
站在当下回望从手抄本向大规模印刷过渡的过程,其间书写技术的物质性逐渐成为作为媒介的物质性,而随着“古腾堡革命”成果的普及,人与物质性的书写活动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基于印刷技术与书籍的传统文学观也随之转变为脱离物理层面的“大写的文学”,使得印刷技术要素以自然而然同时也无关紧要的视觉形式呈现出来。实际上,物质性早已延展出了单个物体的边界,既是社会、文化和技术过程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实践(Bolter:18)。时至今日,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介以及不断走向成熟的数字技术,又带来了新的书写技术、视觉隐喻媒介和虚拟空间,除了延续印刷文本所具有的书写心灵的能力,更实现了与机器的共同协作书写,甚至建立了一种基于人脑协作的视觉—思维反馈环,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文本和文学的生成机制。数字文学也因此成为二十一世纪新的研究焦点。
对于数字文学研究,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策略。一种是杰伊·戴维·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等人的做法,他们倾向于使用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数字文学,如博尔特认为,“后结构主义可以澄清超文本的文化意义”(Bolter:171)。在此类研究中,理想文本、互文性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对于研究数字文学的文本、叙事和审美等特征具有指导意义。但雷恩·考斯基马(Raine Koskimaa)等学者认为,在数字文学和解构主义之间进行简单比附可能具有误导性,会忽视数字文学自身的基本特性,不利于数字文学研究的持续和深入发展(李斌:55)。第二种则是迈克尔·乔伊斯(Michael Joyce)、简·耶洛利斯·道格拉斯(Jane Yellowlees Douglas)、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等学者所坚持的数字文学媒介属性的研究方法,他们在文学交互性、非线性叙事、时间性叙事和本体互渗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凸显了数字文学对于传统文学的挑战与突破(56)。
不论是采取哪一种策略,数字文学研究当中都有着值得从书写的角度探讨的新问题或新动向,例如博尔特探讨电子书写的《书写的空间:电脑、超文本和印刷的矫正》(Writing Space: Computers, Hypertext, and the Remediation of Print),马修·基尔申鲍姆(Matthew G. Kirschenbaum)关于“文字处理”的论述,海尔斯的“书写机器”(writing machine)概念。区别只是在于是否与德里达等人引领的“书写革命”有直接的关联和比较而已。
许多依赖多感官、跨媒介数字技术的艺术实践,也可以结合各类新旧书写理论加以阐释,比如与美国布朗大学的基于洞穴状虚拟投影系统(Cave Automatic Virtual Environment,简称CAVE)有关联的两个艺术创作:沉浸式诗歌《屏幕》(Screen)和投影画作《这(不)是写作》(This Is (Not) Writing)。在前者中,观者佩戴虚拟现实头盔进入实验室后,作品的文字陆续出现在四周的屏幕上,房间内同时响起由人声朗读的诗文内容。随着作品的深入,音效愈发嘈杂,接着墙壁上的文字开始剥离墙壁,朝着观者的方向飞奔而来,观者可以通过肢体动作辅助这些单词归位,也可将它们击碎;当单词剥离得越来越多,观者无暇顾及的单词无处可去,便会散落周围,自行爆破(张洪亮:128)。而在约翰·凯利(John Cayley)创作的《这(不)是写作》中,画家勒内·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画作《形象的背叛》(The Treachery of Images)被投影于三维虚拟环境之中,画作中的烟斗和文字因而悬浮于这一虚拟空间中,并沿着一条处于它们的视觉中心的垂直线旋转。由此,“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要素——文本、语言与阅读——需要全新的理解方式。文本不再局限于纸质页面或屏幕,文本在这一作品中指涉的是承载图像—文字(烟斗—句子)刻印的表面”(李沐杰:69)。这些数字文学研究的书写理论,与跨媒介创作中的书写实践,无疑为未来的书写研究开启了一些新的进路。

《形象的背叛》
本文选自《书写》(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2),此处有改动。由于篇幅所限,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陈静 副教授 专家简介
书写的物质性与媒介—特性分析
早在文字出现以前,人们就利用铭刻在木棍、石壁表面上的记号、符号、图像表示一定的意义,不仅用以辅助记忆,也作为交流的手段。这种书写的技术逐渐内化,与人的内心意识接合,成为一种近乎天然、本能的行为。在从手抄本向大规模印刷的过渡时期,书写技术的物质性逐渐成为作为媒介的物质性;而当“谷登堡革命”的革命性效果已不再明显之时,人们与物质性的书写活动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而数字技术带来了一种新的书写技术、视觉隐喻媒介和虚拟空间。数据及数据库成为文本机制的内在关系,其所构成的虚拟世界为文学自身及文学所构建的世界提供了新的空间。这不仅让人们看到了新技术给传统本质主义文学带来的冲击和改变,也让人们在数字虚拟时代重新审视作为文学观念具象化物质条件和基础的书写技术和媒介自身。
正如凯瑟琳·海尔斯(N. Katharine Hayles)在《我母亲是计算者——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中所指出的,在从印刷文档到电子文本的过程中,“大量的注意力被放在了意义与语言、书目符码的关联上,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意义与数字代码的关联”。虽然不少电子时代的学者们都对之前的作品及文本观进行了反思,但他们的文本观仍是一种非物质性的文本观:“‘文本是什么’这一问题关键中的关键,是相信‘作品’和‘文本’是非物质的建构,且独立于它们所具体化的基质。我们迫切需要重新思考这个假设,因为只要它还未经受质疑,试图说明印刷与电子媒体特殊性的努力就不可能会实现。”(My:97)在这种前提下,海尔斯提出:“一个具体化文本的物质性是其实体特性与其意指策略间的相互作用。”(My:103)此处,文本的具体化是指某种文本类型在某种特定媒介中的实例化,如电子超文本就是指超文本这种文本类型在电子媒介中的呈现。而文本的物质性是一种再概念化的、文本的实体特征与其意指策略之间的互动。比如在考察数字诗歌写作中语言文本的物质性时,语言文本的实体特征就是代码,而其意指策略就是持续的表演,其物质性体现在于代码与其运行之间构成的连续性效果,而这种程序的运行直接影响了界面上的文本呈现、文学意义的生成和观者的审美感受。
海尔斯将这样一种关注文本物质性的批评方法称之为“媒介—特性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她认为这种批评方法保证了关于文本意义的讨论会考虑文本的实体特征,从而重新构建一种新的物质性的文本观念。她还指出这种分析方法是“一种批判关注的模式,认识到所有的文本都是被实例化的,且它们得以实例化的媒介的性质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媒介—特性分析法并不只适用于电子文本,也适用于印刷文本、口语文本等所有参与连续动力学循环的媒介文本类型,因为“若是我们将‘超文本’这个词限制在数字媒体中,就失去了理解一个文学类型在不同媒体中具体化时将如何变异的机会”。海尔斯其实是试图能找到一种能兼顾共性和个性的文本(性)理论,希望能在文本的概念上跨越媒介的限制找到一种兼容性,从而以此把握一种更具普遍性的描述。与此同时,她又不愿陷入一种普遍主义或形而上学的概念陷阱之中,以宏观、抽象的“作品”观一样的概念来抹杀具体化在不同媒介文本理论中所蕴涵的不同意义。
“媒介特性”这个概念并算不上新,文学艺术史与批评一直对它保持关注。海尔斯提出的“媒介—特性分析”可视为媒介研究进入文学/文本研究的具体方法体现,延续的是麦克卢汉以降,以弗德里克·A. 基特勒(Fredric A. Kittler)、戴维·博尔特(David J. Bolter)、艾伦·刘(Alan Liu)、马修·法勒(Matthew Fuller)、列维·曼诺维奇(Lev Manovich)为代表的、对作为媒介的书写与文本的物质性,以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与外在文化机制关系进行本体论意义上研究的脉络。尤其是随着电子文学、电子游戏、数字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等基于数字技术的文艺类型的繁荣,数字人文、数字遗产、文化分析等利用数字技术的人文研究方式的涌现,作为媒介、场域和方法的数字技术在人文艺术创作与研究中的角色、位置、作用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人文研究的热点。但对于如何研究,从何种角度去切入,如何去把握纷繁复杂且各具差异的具体文艺现象,构建一种跨学科批评的可能性,同时又不落入本质主义的窠臼,呈现具体现象和文本的特殊性及其独特机制,就成为数字时代方法论建构的重点。在此方面,海尔斯提出的媒介—特性分析无疑是一种可为借鉴的思路,这不仅因其兼顾了跨学科理论的普遍性与文学作品批评的实践性,提供了诸多行而有效且具有说服力的批评成果,更重要的是,媒介—特性分析为数字时代的文艺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以媒介脉络重新看待技术与艺术、书写与文本、语言与主体、再现与创造等文艺创作的“元”问题,更进而从数字时代的媒介—特性分析去回溯、反思印刷时代的文艺理论批评及观念,这对于建设性地重构长久以来占据主流的基于印刷书籍、人本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理论观念,具有积极的意义。
本文摘自:陈静,媒介—特定分析模型下的电子文学文本生成机制研究,《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2期,40-54。感谢作者与编辑部授权转载。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
李斌 副教授 专家简介
媒介属性与文学审美:数字文学审美理论的建构与发展
传统文学审美理论如何适应新的文学媒介环境?数字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文学审美层面是否保持一致?鉴于数字文学与传统文学在文学创作、形式、传播、阅读和审美等方面的差异,传统文学审美理论对于数字文学审美研究的适用性很容易受到质疑。诸多学者尝试从数字文学与传统文学的差异性入手建构新文学审美理论。
根多拉和谢弗积极从事数字文学审美研究,通过假定数字文学源于“科技社会网络”(techno-social networks)探讨文学审美。科技社会网络指代了数字文学的媒介属性,包括编程操作、计算机化及网络化等。2010年,他们再次指出“过于简单的语境化”将会产生误导,使数字文学研究忽视媒介技术的根本性变化。传统文学与数字文学并非仅是语言风格、叙事方式、传播载体和文学语境等方面的区别。从媒介视角看,由传统文本转变为数字文本,对于文学叙事风格和审美体验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基于数字文本的媒介技术属性,二者将“意向性与机会”“表演与性能”“涌现”“游戏与播放”作为数字文学审美的四个美学基础,并将其视为数字文学“独特的文学性和审美特征,构成网络媒介中人机交流的美学基础”。
数字文学是一种技术指向型文学艺术形式,可能涉及视觉、声音、图像、动画等多种因素,其共性在于媒介技术属性。根多拉二人的数字文学审美研究代表了一种从媒介属性的差异化入手,将数字文学特性作为审美研究重点的学术思路。目前,学界基于数字文学的数字化、算法化、程序化等特征,已探索出多种数字文学审美新理论。

数字文学作品《大海与桅杆》,尼克·芒福特和史蒂芙妮·斯特里克兰德所创作的一个以网页形式呈现的诗歌生成器
(一)程序架构与电子文学美学
菲利普·伯茨认为,数字文学审美研究不能只关注外在形式特征。文学作品外在形式必然拥有与之相对应的内在运行机制。因此,他基于数字文学的程序化构架提出建构“电子文学美学”,并称“它不是文本美学,而是创造美学”。在这种理念指引下,数字文学内在的结构特征和程序功能也是重要审美特征。与传统文学审美多关注文学语言、语义和形式等要素不同,电子文学美学理念视数字文学的程序性、结构性、操作性为重要美学特征。具体而言,伯茨把数字文学创作看作文学材料(亦称“诗性材料”)的编程过程。基于数字文本的媒介属性,数字文学以非线性等特殊结构编排文学材料,形成特殊的文学形式和特征。因此,在数字文学审美研究过程中不能只关注“材料”,还要关注对材料的编排和操作等“元层次”。这一理念的创新之处在于不仅要关注数字文学的表现形式和表面特征,还要突出其内在结构和程序特征。这种研究视角不仅可以理解数字文学作品的意义、内涵等,还可以理解其内部结构、创造性审美及文学动态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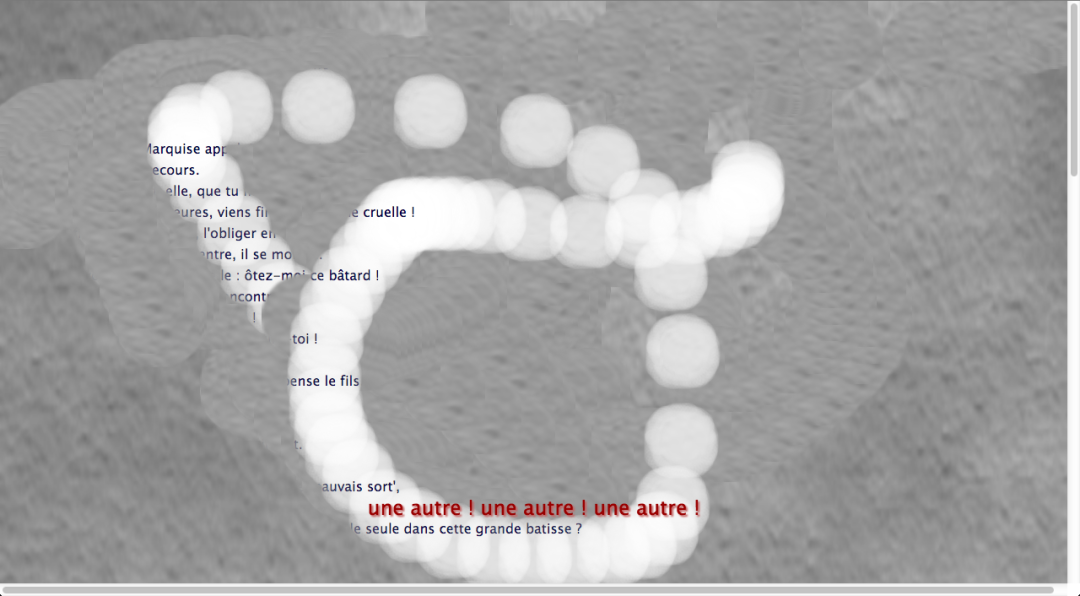
菲利普·伯茨的数字文学作品“Petite Brosse À Dépoussiérer La Fiction”截图
(二)机器结构与电子艺术新美学
弗朗西斯科·里卡多在收集参考多位学者有关文字性作品、互动诗歌、叙事电脑游戏、投影艺术等数十种数字文学作品的学术研究成果之后,提出建构“新媒介批评的契合点和形式”,突出数字文学的媒介特征,强调电子艺术新美学理念。数字文学一部分创造性内容由“机器结构”产生,文学特征和艺术特色受“机器结构”影响。相比于传统文学作品更加注重叙事技巧、文学素材和语言风格等,一些数字文学作品的艺术性和可读性与作品媒介载体的“机器结构”有关。事实上,“机器结构”主要强调数字文学媒介载体的相关特性,如计算机技术、数字编程、程序功能、超链接等,突出数字文学媒介载体在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因此,里卡多认为传统文学理念无法适用于数字文学美学研究,所有形式的电子艺术都需要视其“运行机制”为新美学。相比于传统文学,数字文学媒介载体特殊的媒介属性影响了文学形式、传播、阅读和运行等,也影响了艺术风格、审美特征与审美体验。
(三)创造性表达与电子阅读模式
西曼诺夫斯基专注于数字文学阅读审美研究。他认为“数字作品的首要目的是作为一种创造性表达行为”,阅读应该成为数字文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主张从“电子阅读模式”视角建构文学审美理论。简单而言,电子阅读模式在阅读过程中需要基于数字媒介的媒介属性和媒介特征对文学作品进行广泛、额外的解读。与传统印刷文学相比,数字文学拥有更多表达形式,如程序、超链接、视频、音频等。在数字文学阅读过程中,不仅需要关注语言表达和艺术风格,还要解读其他的艺术表达方式,如超链接、音频、视频等对于文学审美的影响等。对数字文学阅读而言,读者的光标、手势、点击以及情节选择等都会成为文学审美的一部分,构成特殊的阅读审美体验。从学术研究角度看,电子阅读模式不仅展现了数字文学作品的媒介技术特征,还丰富了传统文学阅读理念,使数字文学阅读审美从语言语义分析、叙事风格研究升级为更加全面的研究视角,也使媒介属性和媒介特征成为数字文学阅读审美的重要因素。
总体看来,无论是科技网络社会、程序架构、机器结构还是电子阅读模式,都展现出媒介属性对于数字文学审美研究的影响。正是数字媒介技术独特的媒介特征,如程序化、数字化、超链接等,使数字文学在文学叙事、文学阅读、文学审美等角度与传统文学呈现差异化。
本文摘自:李斌,数字文学审美理论研究及启示:文学性、媒介属性与人机交互,《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2期,55-63。感谢作者与编辑部授权转载。由于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减,注释与参考文献已省略。